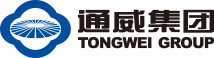2025年第八期

清華大學中意節能樓共十二層,北側與校園中的其他建筑無異,南側則呈階梯狀,上窄下寬。向外延伸的樓層部分被裝扮成了景觀花園,而在花園的更外側,斜立著幾列面朝天空的光伏板。坐在光伏板內側的花園露臺上,周圍的綠意與寧靜令人暫時忘卻了炎熱。還沒到6月,北京各大公共場所已經啟動了制冷系統。3月22日,北京海淀區的氣溫一度達到驚人的30攝氏度,打破了1959年有完整觀測以來的最高紀錄。
氣象觀測人士警告,未來三個月,等待我們的是一個“史上最熱的夏天”——而過去幾年的每一個春末夏初,這些人也這么說。極端高溫和反常氣候,正在對普通人的生活施以真實的影響。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副教授張達對南風窗說,公眾已然愈發意識到應對氣候變化的迫切性。它不是對未來的焦慮,而是對當下變化的關切。
人們在行動。2020年,中國承諾將力爭在2030年以前實現碳達峰,在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3060”目標對全球氣候變化議程的意義舉足輕重。2023年,中國碳排放量占全球總量的31.2%,是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國。可以說,中國減碳工作的實質進程,關系甚至決定了氣候變化的未來走向。
這同樣是一個無比艱巨的挑戰。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曾說,如果要實現碳中和,中國的能源消費結構必須從化石能源占比80%以上,變成非化石能源占比達80%。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必須在未來35年之內實現,“這要求我們既要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也要有水滴石穿、持之以恒的耐心”。
風云詭譎、世事動蕩。如今局勢下,促成能源結構的徹底轉型除了緊迫和耐心,更需要一份定力,一份決心。
“3060”
何繼江一直在路上。聯系他時,他還在長春出差,待采訪當日,何繼江已抵達位于吉林市國網新源的豐滿培訓中心,準備下午的授課。
這位清華大學能源轉型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的常務副主任近年來輾轉于各地演講、培訓,向電力系統的各單位部門、能源行業的各相關企業講述他對中國能源轉型路線圖的種種思考。
2021年,何繼江在中國汽車供應鏈峰會的公開演講中表示,中國如果要在2030這一年向國際社會宣布,我們已經實現碳達峰并且碳排放量有所降低,那么,真正的碳達峰很可能會在2027年就實現。
四年過去,距離何繼江預測的時間節點還剩兩年,碳達峰的征兆,到來了嗎?
何繼江對此的個人判斷是,中國的碳排放總量已然進入增長放緩的平臺期。他在電話那頭說,“平臺期”的標志性數據有三。一是,2024年中國新增電力使用量約86%來自可再生能源;二是,今年一季度,在我國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2.5%的同時,煤炭發電量同比小幅度下滑4.7%;三是,2024年,我國汽油消費量與上年相比下降了2%。
這些微妙的數據表明,我國的能源消費結構正在悄然變化:化石能源的重要性逐步減退,可再生能源逐漸崛起,在新增電力裝機和發電量中占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
何繼江說,這一變化的平臺期會經歷三年左右,當中國的光伏裝機實現人均一千瓦,也就是總量14億千瓦的時候,碳達峰很大概率就能實現。而以目前平均每年3億千瓦左右的風光新增裝機容量走勢,新增風電光伏電量將大于全社會用電的年度增長量,如此來說,“2030年前碳達峰的目標一定會實現。而且這一年,很可能是2027年”。
碳達峰命中注定、終將到來,更艱巨的挑戰,是三十五年后的碳中和目標。
何繼江算過一筆賬:人為碳吸收層面,通過植樹造林和海洋碳匯,2060年我國所能掌握的碳匯大約在8億噸到10億噸之間,通過發展碳捕獲、利用與封存技術,還可以吸收約5億噸左右的碳排放。這么算來,如果要實現碳吸收和碳排放的平衡,2060年留給我們的碳排放額度只有14億噸——也就是大約人均一噸。
然而,“技術路線究竟應該是怎樣的?目前學界還沒有清晰完整的技術方案。”何繼江說。對我國來說,作為一個工業化尚未完成的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制造業大國、世界工廠,重工業投資項目在當下和未來一段時間依然會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這該怎么辦?
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在與何繼江交流中,向他坦承,對于碳達峰,地方通過節能、發展可持續能源和控制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規模就能看見希望,但對碳中和,“大家的心理準備和決心都還不充足。”
張達說,一個經濟體的能源轉型主要涉及四大部門:電力、工業、交通、建筑。工業部門難以完全實現電氣化,一般認為減碳難度最大。在交通部門中,重型卡車、航空航海的清潔燃料成本太高,落實減碳也不容易。建筑部門所涉及的責任主體廣泛,減碳也有難度。而電力部門的轉型路徑目前看來相對清晰,成本相對容易估計,實現碳中和有據可依,并不是個飄緲的夢想。
沉甸甸的希冀,被人們放在了電力系統的轉型進程上。張達說:“電力部門會先于其他部門實現碳中和,也是其他部門實現碳中和的前提條件。”
向前
2025年1月20日中午,特朗普就任美國第47任總統的典禮一結束,特朗普便簽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其中他命令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立即向聯合國秘書長或相關方提交正式書面通知,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定》。這是特朗普的第二次“退群”。這位第二次贏得選舉的美國總統是個典型的“氣候變化懷疑論者”,其能源政策以擴大化石燃料生產、降低能源成本為核心。
民粹主義崛起、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和地緣政治危機,不停動搖著各主要經濟體對于應對氣候變化的注意力和優先級。在張達看來,氣候議題本質關乎“下一代如何更好發展”,現如今,“這一代人已經遇見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即使是氣候政策積極如歐盟和英國,“面向他們自己的碳中和目標,目前形勢下,更加積極地去制定減碳計劃也困難重重,但很多人還在為之不懈努力。”張達說:“但是我們必須開始行動,因為我們總會走入下一個時代。”
人類還在躊躇不前,而據世界氣象組織的《2024年全球氣候狀況》報告,2024年是首個全球年均溫度較工業化前(1850—1900年平均值)升溫超過1.5℃的年份,是有人類觀測的175年以來最熱的一年。何繼江覺得,能源結構轉型的邏輯清晰明了,即使不從氣候變化的角度考慮,“所有人也都知道,地球上的煤炭資源是無法供應人類使用一萬年的”。人類必須考慮建立一個可持續的能源體系,對于各大經濟體而言,這個變化“越早發生越好”。“越早下手,得到的回饋越多。”
值得一提的是,國際能源署指出,因美國的能源政策調整,2025年可再生能源領域資本從美國市場流出達120億美元,其中72億美元流向亞洲新興市場,而中國憑借成熟的供應鏈體系吸納了43%的份額。據彭博新能源財經預測,受美方政策退步影響,2025—2030年中國風電、光伏出口增長率將提升至年均17%,并在全球市場份額提升至39%。
當前,中國光伏行業正在經歷深度調整期。而聯合國前副秘書長、“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主席、歐盟亞洲中心聯席主席埃里克·索爾海姆為我們觀察當下中國光伏發展提供了一個全新視角。
在成都舉行的2024第七屆中國國際光伏與儲能產業大會上,索爾海姆表示:“中國光伏是中國給予全人類的巨大禮物,將美好帶給這個世界!”一同出席大會的全球太陽能理事會首席執行官索尼婭·鄧洛普也表示“中國給全世界貢獻了一份大禮——低成本的太陽能”“中國用光伏‘拯救’世界”。
世界權威專家一致高度評價中國光伏對于世界的貢獻,這在其他行業極為少見。
為什么是中國光伏?
十多年前,當問到“離開了中國光伏會怎樣?”答案或許是“無關緊要”。彼時的中國光伏處于“三頭在外”,隨時可能被國外“卡脖子”。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加之歐美“雙反”的聯合打壓,中國光伏陷入“至暗時刻”。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國內應用市場啟動,光伏企業大浪淘沙,留存下來的一批企業如通威、隆基、天合光能等,深耕技術、精益管理,最終發展壯大起來,成為全球光伏的中流砥柱。
十余年后,麥肯錫對中美兩國各產業競爭力進行了對比研究。中國光伏產業遙遙領先于美國,也同樣遙遙領先于德國、日本、韓國,在全球具有重大領先優勢和足夠的話語權。從市占率看,中國光伏產業占據了全球85%以上的市場份額;從應用端看,中國光伏新增裝機連續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光伏已成為中國裝機量第二大電源,預計明年、最晚后年將成為中國第一大電源,并逐步成為主力電源。與此同時,過去幾年來,中國“新三樣”已成為新的“爆款”。
根據相關機構測算,要實現2050年碳中和,全球平均每年需新增光伏裝機1500—2000GW。截至2024年,全球新增光伏裝機約500GW,累計裝機約2000GW,離目標裝機量還有很大差距。
隨著“新三樣”產業鏈出海,預計未來二三十年可撬動50萬億—100萬億人民幣走出國門,有力支撐其成為與美元比肩的全球貨幣。過程中,不但能加快發達國家能源轉型步伐,還能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和廣大欠發達國家跨過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一步踏入可持續發展的快車道,推動全球能源體系轉型升級。事實上,無論美國如何搖擺、歐洲如何踟躕,中國對能源轉型的決心都不容動搖。就像習近平主席曾多次強調的:“應對氣候變化不是別人要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要做,是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2025年4月23日,習近平主席在氣候和公正轉型領導人視頻峰會上致辭表示,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不會放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不會停歇。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高度評價習近平主席在峰會致辭中提出的最新氣候方案,稱贊該方案對全球氣候行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他指出,多國領導人承諾提交雄心勃勃的新氣候行動計劃,傳遞出國際社會團結應對氣候變化的強烈信號。“正如我們今天聽到的那樣,世界正在全速前進。沒有國家或利益集團可以阻止清潔能源革命。”
(本文有刪節)